
又是一年高考季,我的高考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十年的痛苦和抑郁,换来了中国最顶尖高校的一纸文凭。但是当真的拿到这一纸文凭之后,却反而已经不在乎了——人生就是这么充满讽刺。
高考的阴影
第一次听到“高考”这个词,是上了小学之后不久的事情。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个邻村三十多岁的疯子,跑到学校跟我们这些小孩子玩闹。他一来了就会扯着嗓门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在教室里的我们就知道他来了,下课之后就跟在他屁股红边,用各种小孩子的恶趣味来调戏他。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村子里有名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从小就很勤奋懂事,属于那种家长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家里人一直都以他为傲。而他变成疯子的原因,是由于在当年的高考中,差大学分数线只差了0.5分——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于是就精神失常了。
他父亲为了防止他到处乱跑,就把他锁在家里边,或者用绳子绑起来。但是他还是经常会想办法从家里挣脱出来,只要一出去就会奔着学校的方向。他经常会闯入周边几个村子的学校里边,声嘶力竭地唱着在学校里曾经学过的一些歌曲,或者背诵一些当年课本里的诗词和课文。这个事情发生后,他的整个家庭都被毁掉了。父亲撕碎了他从小到大的所有奖状,扔掉了他所有的课本和读过的书,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每次出门都要躲着学校的方向。这是“高考”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我不明白高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让一个健康、勤奋、优秀的人,一夜之间变成疯子。

稍微大一点之后,高考和大学慢慢就变成了家人在我耳边唠叨的词汇。但是不管父母怎么唠叨,整个童年时代,过得还是非常开心和无忧无虑的,农村的广阔天地,是释放我们天性的舞台。我们在大夏天用竹竿绑着洗衣粉的袋子,去抓树上的知了,然后用铁丝串成一串烤着吃;一帮熊孩子在田野中找到田鼠的洞穴,使劲往里边灌水,等到田鼠实在撑不住跑出来时,我们一把掐住它的脖子,然后扒掉它的皮;还有树上的麻雀,水里的鱼,草地里的兔子,都变成了我们嘴下的烤肉……
底层的艰辛
直到上了初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当这种可能是叫做“自我意识”的东西觉醒之后,生活的压力和重负,一下子向我袭来。那些年,我们当地出去打工的很少,基本上都还是靠种地为生,而人均耕地又很少,那点种地的收入扣除沉重的税费和生活开销之后就基本上不剩什么了。
读小学的时候,我一直对学校怀有一种恐惧的情绪。因为一到开学的时候,我妈就要带着我去找校长要求缓交学费。记得当时是一学期一百多的学费,对于我们家来说,已经是比较沉重的负担了,我妈经常要和校长软磨硬泡好长时间,才能让校长答应。即便这样,班主任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经常会唠叨:某某同学的学费还没有交,回去赶紧再催一催自己的家长吧——这对孩子来说,还是一件满伤自尊的事情。那些年,父母经常东奔西跑,到处去打零工,才能挣得一点可怜的钱维持基本的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父母也经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生活琐事而吵架。我经常半夜被他们吵架的声音吵醒,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父亲经常唉声叹气的,身体也不好。
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会因为0.5分的问题,就一下子疯掉。在他那个年代,能不能考上大学,对于出身底层的人来说,基本上意味着两种命运。考上了大学,那就意味着你跳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门”,成功地跻身于城市和中上流社会。而如果考不上大学,那等待自己的,将是非常艰辛而残酷的命运。那个看起来可以忽略不计的“0.5”分,隔开的是两个世界。
我自小性格柔弱,在父母和亲人看来,不是那种在社会上可以“吃得开”的人,所以他们就很担心我未来的生存问题。父亲经常会半开玩笑地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可怎么办呢?在那个时候,我也看到了小时候带着我无忧无虑玩耍的哥哥姐姐们,在踏入社会成家立业之后,被沉重的生活负担累弯了腰,被压得喘不过起来。我陡然产生了一种对未来的恐惧情绪,这种恐惧感像毒药一样,慢慢开始吞噬我的心灵。而且,当我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之后,一下子感受到了一种对于父母的强烈的歉疚感和负罪感。当时虽然学习成绩总体上还比较好,但仍然是比较贪玩的,父亲朝我发过好多次脾气。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对不起父母的辛劳,我应该用我的勤奋和努力,让自己的家庭将来能够过上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而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高考。
走上抑郁之路
从进入初二开始,我就开始下定决心发愤读书——悲剧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我的性格看起来比较柔弱,骨子里却是一种“要不不做,要么做绝”的行事风格。既然我要努力了,那我就要努力到极致——当然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得不为。
我当时就读于我们村子里的那个初中,校舍都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了。我初二的时候坐的那个座位,一到下雨的时候,外边下大雨,我那个座位就下小雨,雨不是特别大的时候,我就静静地欣赏雨滴滴到课桌上的那种美景,要是雨下得太大,老师就让我把桌椅搬到最后一排去避雨。有一次雨下得实在太大,学校就给我们放假了,因为担心校舍会在暴雨的冲击下坍塌(这在之前是发生过一次的)。当时在学生中间,流行着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绘的那种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初中的孩子,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都有着比较强烈的暴力倾向,打架斗殴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一个发小当时因为一些小矛盾,和另外一个同学约架,结果砍了那个同学一刀,虽然没有引起太严重的后果,但还是到外边躲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的老师为了能够以暴制暴,自己自备了钢管作为教学武器。还有个初三老师一边上课,一边偷偷在外边贩毒(我们当地的一种劣质毒品),结果在课堂上就被带走了。这就是我当时所就读的农村初中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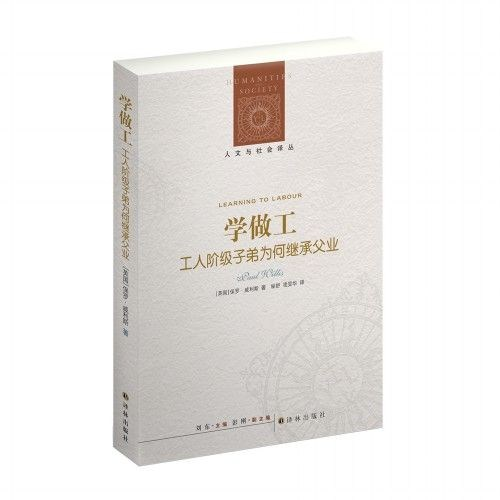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当地重点高中的名字,所有人辛勤奋斗的目标,就是能够考上县里的普通高中。我们一届学生有两百多人,能够考上那所普通高中的学生,在10个以内;而上了普通高中之后,考上大学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即使考上大学,也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差的学校。
所以我强烈地意识到,在教育质量如此之差的情况下,我如果想要考上大学,一定要付出超出别人很多倍的努力才行。自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成一架考试机器。我每天都给自己下康德式的绝对命令,我要求自己除了非常必要的交流之外,一句废话、闲话都不能说。我从早到晚把自己封闭起来,上课学习,下课也学习,平时学习,周末和假期也学习;我屏蔽掉和别人的正常交往,摒弃掉一切跟考试无关的兴趣爱好,不看电视不看小说不打球不运动,不把心思浪费在一切非学习的事情上。我不仅追求这种达到极限的学习时间,还要把每一分每一秒的学习时间利用到极致,上课如果偶尔走神或者打盹,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把自己谴责很多遍。
这样一种极端的学习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成绩只是属于中上等水平,等到中考的时候,已经比其他同学高出一大截了。我这一届最后考上县里普通高中的有八九个,其他同学都是刚刚超过普通高中的分数线,而我则是差一点考上重点高中。
在成绩越来越好的同时,我的精神状态也慢慢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到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太疲惫太疲惫,感觉快支撑不下去了,但是我依然需要强撑着。我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弥漫在我的心中一直无法排解。家里人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太过于内向了,一直希望我不要老呆在家里看书,要出去和同学一起玩,可是我已经丧失了与人正常交往的能力。周末回家的时候,我就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呆烦了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在空旷的乡间公路上骑来骑去,从东边骑到西边,再从西边骑到东边,这样来往反复。有时候遇到下雪,我就一个人在一片茫茫雪原中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之后,再一个人走回来,一路上只能看到我和麻雀的脚印。
被异化的考试机器
在这种状态下,我进入了高中。那时的我,心力已经被严重透支和耗竭,已经没有了一开始的那种冲劲和精气神了。可是此时我已然彻底把自己异化成了一个考试机器,如果一旦脱离这种生活,我反而会感觉到无所适从。从高一开始,我就基本上是在以高三的状态在学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抑郁症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我无时无刻都在被各种负面情绪笼罩着。我经常会莫名地感觉到胸闷,一种非常压抑、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有一次在教室里上晚自习,这种胸闷的感觉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向老师请假回了趟家。家里人以为我生病了,带我去医院检查,可是却检查不出任何毛病。那段时间,我反而比较喜欢生病的感觉,因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我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让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短暂地休息一下,所以我经常是盼着生病,生病之后的精神上的轻松感已经压过了生理上的那种痛苦。

一般来说,对于得抑郁症的学生来说,成绩都会出现断崖式下滑的状况。可是当时的我成绩不仅没有下滑,反而一直稳步提升。无时无刻的负面情绪萦绕在我心中,严重干扰着我的正常思维。为了不耽误学习,我只能把负面情绪强压下去,而强压下去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大脑停止正常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一种非常笨拙的方式来学习。高一的时候,我能把两本近现代史一字不落地从头背到尾,其他科目达不到这种程度,不过也大体差不多。对于理科科目来说,我也是一样的学习方法。我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思维来解题,那我就一道题一道题地死记硬背,我一天抄一百道数学题,把同类型的题放在一起抄一遍又一遍,达到看到这样的题就能够条件反射地知道怎么解的程度(这种方法推荐给跟我一样笨笨的同学来使用,我数学高考成绩最后是144分,亲测有效哦)。可以说,我每一分的成绩,都是用十倍于别人的努力拿到的,而每一分这样的努力,都使我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更大的摧残。
用这样的方式,我在我的高中里创造了一个传奇。高一一年,我从全县五十多名一直考到全县第二再考到全县第一,高二高三两年总共八次统考考了八个第一没有一次失手,最高的时候能比我们班第二高出一百多分。在高三全地区十几个县市的大统考中,我已经能够跻身前三名,达到和重点高中的尖子生并驾齐驱的程度。我在学校里享受到了学生所能够享受到的一切优待和福利,我被免去了学费、住宿费等一切费用,吃饭也可以在教师食堂里边和老师们一起免费吃饭,快到高考的时候学校还让我从宿舍里边搬出来,单独给了我一个房间。
尽管有这么多的成绩和荣誉,可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甚至都已经遗忘了当初这么发愤的动力和意义了,是为了高考,为了父母,还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都不重要了。高考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我已经不在乎了,对于高考结束后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我所做的,只是履行一个我作为一个考试机器的所应该履行的职能而已,这本身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的意义所在了。我潜意识里,经常觉得我注定是会英年早逝的,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不会感觉到一点痛苦,反而平静地认为这是我应有的结局。
就这样我走进了高考的考场。在某一门的考试中,由于巨大的精神压力,我犯下了一个极为低级的重大失误。最后的结果是,我以几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调剂到一个相对比较差的二本高校。而我们班五十多人中,加上我只有四个同学考上了大学,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三个同学都是刚过二本线。
绝望的挣扎
当从高考考场中走出来之后,我突然间变得很迷茫。支撑我这么多年的信念一下子没有了,我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是什么。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每天在家里呆着不知道该干嘛。我觉得我应该调整心态,我觉得我应该开心一些,可是总是处于这样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后来走进了大学,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和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感觉到了极大的不适应。在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进入大学三个月后,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我每天都在与非常强烈的自杀念头搏斗着,我去过颐和园,在昆明湖边徘徊了很久;我考察过我们学校十层以上的教学楼;我站在五环的立交桥上,看着桥下来来往往的车流……
在一次蓄谋策划的意外事故之后,我终于如愿躺到了医院里边,可是我需要面对的,是更多的误解和更大的精神压力。而我此时依然不知道,我早就已经患有极为严重的抑郁症。在医院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办理了休学回到家里,开始了一年生不如死的噩梦般的生活。我每天都在床上躺着,从早躺到晚,承受着生不如死的煎熬,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干不了。当时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应该就这么报废了,以前的种种努力和奋斗,都显得那么可笑。我不敢面对过去,也不敢想象未来。爸妈那段日子也都很无奈,他们说宁愿我不上大学,哪怕呆着在家里边种地,也不愿看到我这样。
后来家里才慢慢意识到我可能是得了抑郁症,带我找了一些中医来治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是喝了一些中医治疗神经衰弱的药物。我自己也慢慢努力地让自己恢复起来,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间长了之后,心里的阴霾慢慢散去,开始恢复了一些生命的活力。在复学回到学校后,虽然表面上已经能够正常地学习生活,但是那种抑郁的情绪一直长期纠缠着我。
另外一条道路
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与北大齐名的另外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当我最终拿到那张硕士毕业文凭的时候,我已经被抑郁症折磨了十年了。十年生不如死的抑郁、痛苦和煎熬,换来了这么一纸文凭。但是当真正把它拿在手里边的时候,却已经不在乎了。
高考结束后很多年,我一直逃避一切跟高考有关的话题。每年到高考这两天的时候,网上铺天盖关于高考的评论总会勾起我的一些记忆,让我异常痛苦。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敢回忆自己的青春和过去,我害怕面对过去的同学和朋友,我希望能够把那段经历从我的记忆中彻底切除。整个青春时代对我而言就是一场噩梦,或者说我是一个根本没有青春的人。
现在平静下来想一想,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是没有别的选择的。对于一个出身寒门的学生来说,我只能用十倍于别人的努力,来弥补家庭出身所给我带来的结构性不公平。如果我不在学校里将自己异化成一个考试机器,用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来换取改变命运的分数,那就只能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接受另外一种更残酷的异化——这是我大部分同学和亲人的的命运。

当然,在社会阶层已经固化的今天,我所有的这些奋斗和努力,也并不能真正改变我自己和家庭的现实命运,只不过是把从一生下来就套在我身上的链锁稍微松动一下而已。我的这些经历,既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我所出身的这个阶层的悲剧。我痛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要为资本的利益遭受异化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痛恨这样一种人和人之间狼一般的社会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痛恨这样一个用甜蜜的诱饵摧残人性却无法真正实现阶级跨越的教育制度。所以,我并不因为我通过自己的个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拿到的那一纸文凭而沾沾自喜,也并不寄希望于通过这一纸文凭过上一种把底层劳动者踩在脚下的“肉食者”的生活。不改变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我所有的个人奋斗终归是狭隘、自私的,所能起到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
就像马克思在他17岁那篇毕业论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愿意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把我的一生、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改造不平等社会结构、把人类从残酷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壮丽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这是一条注定艰辛而坎坷,却一定会胜利的道路。当将来的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一定会为现在的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无比自豪——这是对我十年抑郁之路的最好报偿。